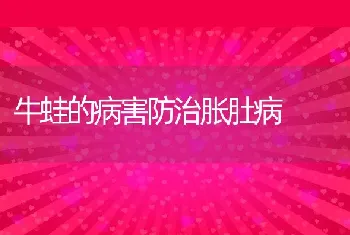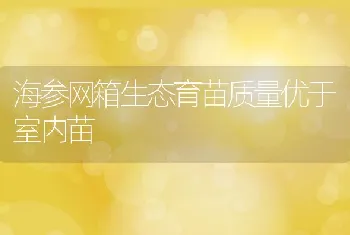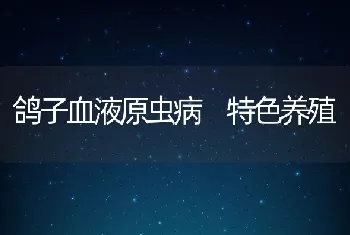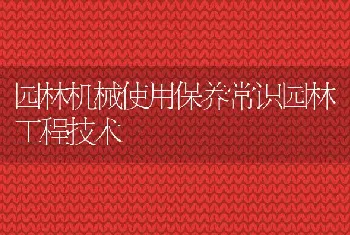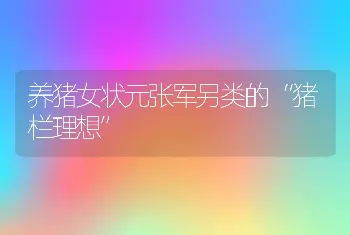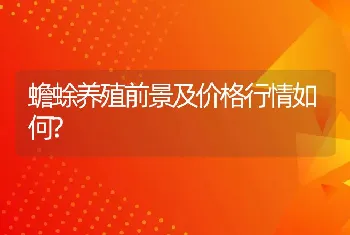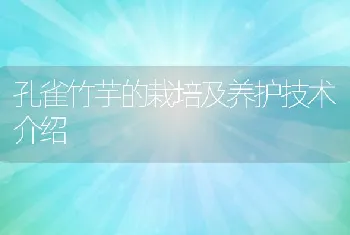那年我十九,在辽南的一个叫丁屯的村里当青年点点长。从青年点往南走一百多米再折向东就上坡了,那坡是东山延伸下来的脉络。“老五保”的家就在脉梢上。

那是一间土房,经年风雨已使墙面斑斑驳驳,门扉是几根木条钉的,开起来直悠忽;窗上没有玻璃,贴的是窗户纸,所以看不见外面的事,大概他们也不想知道外面的事儿。

“老五保”是老俩口,村里人都叫他们二爷二奶。二爷大约八十岁左右,瘦骨嶙峋,须发稀疏,语言也像须发一样少;二奶七十多岁,一脸的笑模样,滿嘴没有一颗牙,却特别的爱说话。他们的家庭成员还有一口,那就是一条黄狗,像二爷一样瘦骨嶙峋,却抖擞着精神。

我第一次到“老五保”家,是在一个黄昏。刚到坡上,就见那条狗倏然立起,连叫几声,然后就狗视眈眈地盯着我的一举一动,并从喉管里发出一种低沉的吼声。一个老太太从屋里出来,那是二奶,也不知她喊了一句什么,于是那狗就很友善地走到我的跟前,嗅嗅我的裤腿,大约是表示礼貌。

“老五保”家除了一个柜子,一张饭桌外,几乎家徒四壁,可老俩口过得还挺乐呵,一把青菜一碟酱,还你敬我让的,剩点汤汤水水就喂狗了。就从那天起,我开始给“老五保”家挑水了。从此“老五保”和狗就和我亲昵起来。“老五保”家生活清苦,那狗就跟着寡汤淡水的,可它却从来没有淡薄职守。有时青年点剩点饭菜,我就喂喂那狗,有时候从公社供销社买点像石头一样硬的小饼干,也塞它嘴里几块,这时它就高兴的往我怀里拱,像孩子似的。

秋天的时候,队里组织人夜里“看地”,谁都不愿意被编在后半夜,我自报奋勇。那天夜里,我手握镰刀,头上套着一个苹果筐,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两边是一人多高的庄稼。月亮隐在云里,夜风掠过,苞米地黑影憧憧,任何一点声响都让我心悸。突然,我的身后响起“沙沙”的声音,我快它也快,我慢它也慢,顿时我的每一根神经都繃紧了,毛发竖立,此时任何畏缩、胆怯都没有用了,更不容我多想,我扬起镰刀,猛然转过身去,呀!是那条狗。我心中一阵惊喜,它来的太是时候了。它定定地望着我,眼睛泛着亮光,似乎在问:你为什么深更半夜走在野地里。我搂着它的脖子,拍拍它的背,表示对它的赞赏。在这漆黑的夜里,我蓦然觉得自己有了胆气。可它是怎么发现我的呢?它当然不说。它静静地走在我的身边,而我走在静静的夜里,空气里有庄稼的清香,夜色真美。

第二天夜里,我走出青年点的时候,轻轻地打了一声口哨,它旋即一阵风似的出现在我的面前,于是我们出发。这个秋天,我有了快乐的夜和难忘的记忆,因为它伴随着我。第二年的秋天,我抽调回城了。半年后听人说二爷二奶都故去了,心中一阵酸楚,突然萌发出回村看看的念头,于是踏上了回丁屯的路。

快到村头的时候,有两个人牵着一条狗与我擦肩而过,那条狗突然扭过头来定定地看我,不肯走,眼里滿是凄然无助的目光。呀,那是二爷二奶的狗呀,那是我的伙伴呀,它认出了我,可我一时竟呆在那里毫无办法,眼睁睁看着那两个人用力将狗拉走了,走远了。望着远去的狗影,我恨,恨我自己无能,顿觉心中空落落的。

45年过去了,世事纷繁,许多的人、许多的事儿我都淡忘了,但这条狗,这条连名字都没有的狗,这条土生土长土一样颜色的狗,却依然守护着我的心扉。